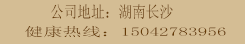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螳螂 > 螳螂的习性 > 群山雷杰龙短篇小说记骨一澎湃在线
当前位置: 螳螂 > 螳螂的习性 > 群山雷杰龙短篇小说记骨一澎湃在线

![]() 当前位置: 螳螂 > 螳螂的习性 > 群山雷杰龙短篇小说记骨一澎湃在线
当前位置: 螳螂 > 螳螂的习性 > 群山雷杰龙短篇小说记骨一澎湃在线
作者简介
雷杰龙,年生于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年至年进修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居昆明,供职于《边疆文学》杂志社。年开始文学创作,在《人民文学》《钟山》《花城》《江南》《大家》《诗刊》《滇池》《当代文坛》等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百余万字。
01
大唐大历九年(公元年)早春,寒风凛冽,河北遂州人杨仲翔身在远离故乡数千里之遥的蜀南眉州彭山县,在一条小溪边为朋友吴保安夫妇洗骨。他把二人的遗骨分别从两具简陋的薄棺木中取出,在溪水中一根根,一块块地擦拭清洗。洗净之后,再按人体骨骼组成次序小心翼翼排列在一起,在清冽透明,微有暖意的阳光中晾晒。
为吴保安夫妇洗骨之时,杨仲翔垂首低目,莫名悲伤。眼花腰疼时,他会直起腰来,举头望天。天空辽阔,青天高远。二十年前,经过大唐京师长安城,他也曾如此仰望,不仅仰望苍穹,也仰望青天之下高高在上的大唐天子——玄宗皇帝李隆基。
可如今,他却质疑二十年前那样的仰望有何意义?为了那样的仰望,他和朋友吴保安,以及无数的芸芸众生,承受了不堪承受的命运之重。而到最后,一切的仰望都如眼前,都得低下头来,面对别人和自己在时光淘洗之下遗留的,轻若无物的几根骨头。
02
杨仲翔依稀记得,经过朱雀门的时候,杨仲翔和同行的其他军人忍不住伸直脑袋向上仰望。那是大唐天子李隆基站立的地方,也是他高高在上俯视长安城芸芸众生,万千百姓的地方。杨仲翔听说,只是听说,皇城里面是三省六部的官署衙门,再后面是太极宫,太极宫东北方是大明宫,太极宫和大明宫后面是皇家禁苑。杨仲翔知道,那些地方自己此生永远无法踏足,但它们却决定着无数像自己这样的人此世该走向什么样的地方。正如那个时刻,他从家乡河北遂州启程,一路西行,途径许多州县,过西京洛阳,入函谷,经华阴,进入关中大地,来到长安城,在城外露天扎营一夜,一大早便和大军一起动身,经东城春明门入城,一路向西,走到皇城朱雀门楼下,步入当今天子的龙目俯视之中,自己和7万军人一路跋涉经过的行迹,便是从皇城中发出的征讨南诏一纸诏令决定的。对于那一纸诏令,杨仲翔曾在军营大帐和龙武将军、新任的姚州都督李宓等人一起谈论过。他们明白那一纸诏令的用意。前几年,南诏蛮王阁罗凤野心膨胀,袭杀了姚州都督府都督将军张虔陀,攻陷了姚州都督府,朝廷诏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大军征讨,结果惨败而归。这一次,朝廷再次征招河北、河南两道和长安、洛阳两京地区的青壮勇武之人,得兵7万,汇聚京师长安,从这里出发入蜀,会同何履光将军率领的岭南五道大军,再次征讨南诏,意图恢复姚州故地,一举击灭南诏国。因为有鲜于仲通大军征讨溃败的前车之鉴,杨仲翔和李宓将军都清楚即将开始的征讨必定是一场险阻重重的苦战。但他们同样明白这次征讨必不可少。如果对南诏袭杀张虔陀,攻陷姚州都督府之事放任不管,那南诏必将做大,和西南的吐蕃联手,一同骚扰攻击大唐腹地,剑南节度使控制的巴蜀地区。若巴蜀地区陷落,那将直接危及大唐京师长安所在的关中京畿要地。纵使放下这些不论,任大唐边疆的一个蛮王袭杀朝廷命官,夺地占府而不闻不问,也会有损朝廷威严,让大唐广袤边疆地区的那些地方豪酋们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四处作乱,那样,大唐天下将永无宁日。所以,那一纸诏令是必须的,7万大军踏上征讨南诏之路也是必须的,即使其中必将有许多人埋骨他乡,再也无法回归故土也是必须的。而对于杨仲翔来说,那一纸诏令更是必须的。因为那一纸诏令意味着建功立业的机会。虽然他在家乡遂州饱读诗书,尤其留意那些兵事权谋之术,自负才华,但因出身寒门,若没有那一纸诏令,要想通过征辟科考进入仕途,甚至有朝一日来到京师,进入皇城六部衙门之中,那是绝无可能的事情。即使到边疆地区从军入幕,那也得看机会。而那样的机会同样极为渺茫。好在有了天宝十三年(公元年)早春的这一纸诏令,他才有机会变卖家资,打通关节,到龙武将军李宓帐下当了一名普通的行军参军,负责参谋和打理文书之事。而这个机会的获得,还得拜南诏莽荒边远和鲜于仲通之败所赐,他明白,若不是许多和他一样想当参军的人对此望而却步,以他的微薄声望和贫寒门第,根本不可能入幕参军,站立在李宓将军身边。
杨仲翔还记得,大军走过春明街,过了朱雀门,经过明德街,出了西门明德门,就离开了大唐天子的视线和长安城,正式踏上了征讨南诏的道路。一出长安城,严整的队伍就开始松懈了,许多人开始唉声叹气,不停抱怨。正午时分,大军到了咸阳城边,来到渭河桥头,送行的队伍挤满桥头桥尾和两旁的道路。咸阳桥又名渭桥、霸陵桥,是长安人送别西行南往之人的所在,所谓“霸陵伤别”,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从来都令人伤感。不过,对此他并不挂怀,他的亲友远在遂州,不会跑到这里来送别。再说,从军是他的意愿,壮行的离别酒他早在遂州出发时就痛快喝过了。但眼前的场景还是让他吃惊。这样的场景不用多说,十五年后,他将含着泪水在杜子美的《兵车行》中重温“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样的场景。而在当时,当诗人杜子美站在道旁,目睹眼前情景,酝酿着这首诗的时候,杨仲翔心中并无多少感受,他只是暗中思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这样心甘情愿地前去打仗,对大多数普通士兵而言,他们只是普通的儿子、丈夫、兄弟,征讨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只有能否活着回来的事情,天子的宏图远略,将相的功名成败这些闲事统统和他们无关。看着眼前的场景,杨仲翔的心中闪过一丝寒意:大军士气如此,会不会是个不详之兆?这个念头闪过的瞬间,他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身旁的李宓将军。李宓将军若有所思,眉头紧锁,神情严峻。他不知晓,那一丝寒意,那不详的念头是不是也在同一个时刻,闪过李宓将军心头?
无论心头是否闪过那样的念头,作为7万大军的统帅,李宓将军只能坚韧不拔地履行大唐天子进攻南诏的诏命。过了咸阳,大军进入汉中,经艰险的秦岭栈道开赴蜀地,稍作休整,补充粮饷军资,便又开拔,渡过金沙江,经过血战,攻占了姚州都督府,很快打到了南诏国的王城要害之地——苍山洱海地区。在洱海东岸,李宓的大军和左武卫大将军何履光率领的岭南五道大军会合,一起商讨攻打南诏都城——太和城的方略。大家明白,之前的战事都是攻打南诏之战的前奏,眼前的一战才是决定成败的最后一仗。南诏王阁罗凤知道以自己的兵力无法和大唐大军正面交锋,已经把所有兵力收缩集中在苍山脚下,洱海西岸的苍洱之地。这片地区是天险之地,西有南北横陈高峻险拔白雪覆顶的苍山诸峰,东有纵贯南北烟波浩渺的洱海之水,北有山海挟制之间的龙首关,南有山海相应,前面还有一条天然的护城河——洱海的出海口西洱河——环护的龙尾关。在苍山洱海和龙首关、龙尾关之间,是南北铺陈达数十里的广阔平坦,物产丰腴之地。在这片广阔之地的中段,坐落着南诏的王城——太和城。面对眼前的情景,李宓将军、何履光将军和众多将军、参军们明白南诏的王畿之地是一座天造地设的大城,南北横陈数十里的苍山诸峰和烟波浩荡的洱水是这座城池的西城墙和东城河,但这两段城墙和城河,大军根本不可能涉足。唯一剩下能够攻打的地方便是龙首关和龙尾关。这两座城关就像苍洱大城的北大门和南大门,只要能够破关而入,太和城便将袒露在大唐的锋镝之下,无险可守,不攻自破。但这两座城关地形险要,地势狭窄,大唐军队虽然兵多将广,但却难以展开,各种进攻手段难以施展,南诏虽然兵少,但防守却不太艰难。既然如此,那是否可以采用围城之策,让南诏王坐以待毙?大家稍一思忖,便明白这绝不可行。以苍洱大城地势之大,物产之丰,就是围个十年八年也能衣食自足,而大唐十余万大军却绝然耗不了这么长时间。别的不说,那么多粮饷耗费就是大问题,再加是上久攻而不克,天子必会震怒,更别说将士们远离故土,思归心切,数年下来,必会士气耗尽,不战自溃。所以,剩下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只能急战,以雷霆之势破釜沉舟,硬攻龙首、龙尾两座城关。只要能攻克其中一关,其余一关和太和城便将难以防守,南诏王就将束手就擒。在洱海东岸的营地,李宓和何履光两位将军划分了职责,由何履光攻打龙尾关,李宓攻打龙首关。而全力主攻,则在龙尾关。只要龙尾关一破,大军便可直取太和城,直接攻打南诏王阁罗凤。李宓将军不能用全力攻打龙首关,是因为必须分兵防备北方的吐蕃军。在大军进攻南诏的同时,吐蕃大军开始南下,在大唐北路大军的背后虎视眈眈。大家明白,必须保障北线唐军的安全,在吐蕃军攻破北线唐军之前攻破南诏。只要南诏一破,企图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坐收渔翁之利的吐蕃军便无机可乘,必然退兵。而防守北线的关键在邓州城。所以,北线李宓大军并不能全力攻击龙首关,而只能在尽力攻击龙首关的同时分重兵把守邓州,以求万无一失。
很长时间里,百无聊赖的杨仲翔都在心里复盘南诏之败。但这样的复盘已经毫无意义。攻击龙首、龙尾两关遇到的挫折都是意料之中的。虽然对唐军来说利在急战,但这本来就是一场消耗战,如果不经过长期持续攻击,根本不可能攻破两关。但朝廷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催战的诏命一道接一道下达。既然攻击两关受挫,那就得开辟攻击的第三条路线,点苍山不可逾越,那就只能在洱海东岸造船,从水路攻击。但造船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况且来自北方和岭南腹地的大军里也缺少造船的工匠,即使昼夜不停赶工,耗费数月,所造之船也仅粗具规模,勉强堪用而已。但还未等水军练成,船队便被乘夜而来的南诏水军偷袭,一把火烧光。这自然是疏于防备之过,但也实在是防不胜防。再说,造好的那些船,不过能载三两千人而已,南诏船队昼夜不停在海上巡视,这点兵力即使能够全都渡海登岸,也无什么大用,只不过白白耗损而已。船队被毁,责问催战的诏书又到,海路不通,只好再次加大攻击两关力度。因龙尾关更加险要难攻,只好在攻龙尾关的同时,抽调更多兵力攻击龙首关。偏偏此时,军中疫病流行,军力吃紧,不得不从邓州抽调兵力攻击龙首关。对此,他曾提醒过李宓将军,认为此举不妥。但李宓将军无奈,说没办法,战事旷日持久,朝廷催得紧,战局如此,他也只能赌了。再说,唐军困难,南诏军难道又轻松了?连日激战,他们也早有困顿疲惫之态,或许奋力一击,便能破关成功。只要破关成功,便不用惧怕吐蕃。结果,面对唐军猛攻,南诏不得不从龙尾关抽调兵力增援龙首关。这样,龙尾关兵力减弱,何履光军乘机猛攻,一举攻下龙尾关。眼看南诏之战即将取胜,但正在此时,邓州被吐蕃军攻破的消息突然传来。之后的战局便崩溃了。何履光军从龙尾关进攻太和城而不克,与此同时,吐蕃军从北线唐军背后发起猛攻,龙首关南诏军也全力出击,北线李宓大军便被两军夹攻而溃灭。李宓将军战死。杨仲翔持刀奋战,受伤力竭而被俘。李宓军破,何履光军只能急速撤退,大唐天宝伐南诏之役就这样以惨败收场。
如今,大军过朱雀门仰望天子的情景早已依稀模糊,心中复盘战败的差错早已毫无意义,此生的功名也早已尽归尘土,杨仲翔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奢望:回归大唐,埋骨家乡。但这样的奢望也只能是奢望了,能够实现的希望早已渺茫得犹如抓住天边的浮云,可望而不可及。被俘后,他的身份再也不是大唐军中的参军,而只是一名南诏土酋的家奴。被俘之初,他还抱着一丝希望,以为大唐还会再次发兵攻打南诏,至少,也会威逼南诏达成合议,其中必有释放此战被俘之人的条款。但大唐没有派兵前来讨伐,相反,南诏军却不断北进,攻击剑南节度所辖的蜀南地区。不久,在为奴的不堪日子里,传来了安禄山、史思明叛乱,洛阳、两京沦陷,明皇天子仓皇入蜀的消息。接下去的日子里,大唐乱成一锅粥,有谁还会念及天宝伐南诏之役被虏之人的事情?其实,被俘之后,杨仲翔早已明白,自己已经成为没有名姓的人。被俘之后,伤还没好,他就和许多战俘一样,在南诏军的刀剑押解之下,和许多南诏人一起收敛大唐阵亡将士遗骸。那么多的阵亡将士,情景惨不堪言。他们先是在战地挖一个个大坑,再把散落附近的将士遗骸收集起来,一具又一具地放在坑里,小的坑里放数百具,大的坑里放上千具,再大的坑里放数千具。这些坑被土石填平,堆垒,垒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小山包。除了主帅李宓将军单独掩埋,垒墓立石刻碑之外,小山包下埋的人全都没有名字、籍贯,所有的人都是一个人,全都是无名之人。杨仲翔明白,如果他阵亡了,也是万千无名之人中的一个。而即使活着,死了之后埋骨异乡,他也同样将是一个无名之人。要想死了之后留下名姓,他只有回到家乡埋骨故土一条路。其实,死后是否留下姓名他早已不在乎了。不用说什么粪土当年万户侯,在亘古的日月交替,时序代迁之前,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死后无不都等同于尘土,单是眼前埋骨异乡而无法留名的万千将士,就让他明白自己身后是否留名实在是无聊透顶之事。他想回到故乡,是因为双亲在堂而无法奉养,妻子和一儿一女在家而无法相见。这是让他痛彻心头之事,也是他梦想回到故土的唯一理由。
但回到故土已近乎绝无可能。被俘不久,他就有了第一个主人,那是南诏军里的一个领主,因为抗击唐军有功,杨仲翔和其他上百名战俘被南诏王赏赐给他为奴。那个人很细心,一一详查每一名战俘的来历。查问到杨仲翔时,他一眼就看出杨仲翔读过书,迅速查出他是唐军中李宓将军帐下的一名参军。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威胁不给大家吃饭,从其他俘虏之口查出杨仲翔这个参军是怎么来的。原来,杨仲翔是大唐宰相杨国忠的远房侄子。杨仲翔变卖家资,打通关节找到杨国忠,向李宓将军举荐,才成为李宓将军帐下的一名参军。那位主人得知这些关节,兴奋不已,开出了绢一千匹的高价赎金,逼着杨仲翔写书信,以为能借此大发一笔横财。杨仲翔对他说,他的书信不可能送达杨国忠手上,那封信即使写了,要到达杨国忠之手,不知中间要通过多少关节,其间消耗的钱财就不只一千匹之多。退一万步说,他那所谓的杨国忠远房侄子是七拉八扯才攀附上的,如今,他应该早就忘了他这个名叫杨仲翔的人,那封信即使到了他的手上,他也会不屑一顾,随手抛弃,绝不可能为他付那么多赎金。主人说,那你就给家里写。杨仲翔说家资早就变卖一空,即使家里得到书信,也不可能再付什么赎金,只不过给家人徒增忧虑烦恼而已。主人说,那你给别的亲人朋友写,反正总得写,赎金一匹都不能少,如果不写,你和别的那些俘虏都休想吃饭,从今天起,先让你们饿上三天试试厉害。无奈,杨仲翔只能写书求赎。但给谁写呢?思来想去,杨仲翔想到一个人,他姓吴,名保安,字永固。
03
杨仲翔和吴保安素不相识。他知道这个人,是在大军经过剑南节度,驻扎在成都短暂修整的时候。那时,他突然接到一封书信,是从蜀中绵竹县寄出的。那封信里,那位名叫吴保安的人写道:“遂州故人入蜀,告知足下在征蛮军中,奉职李将军帐下。听说你是乡人中的翘楚,有幸和你同乡,虽然尚未拜访,但心中常怀秉仰。听闻你是杨相国的侄子,又是李将军幕府中的大才,因为德能显著,才受领李将军幕府中的重任。李将军文武兼备,受天子之命专征,亲统大军,将平小寇,以李将军英勇和足下的才能,大军取胜,大功告成,旦夕之间便能完成。保安幼而好学,长大后专心经史,可惜才能匮乏,只做了这里的一个小小县尉。绵竹僻处剑外,离家数千里,关河阻隔,在这里本已不堪,可还是到了任期将满之时,后面到哪里任职,难以期待。以我的不才,想要通过考核选拔,到别的地方任职升迁,得到另外一份俸禄,实在不敢奢望。可就此回家,归老田园,辗转死在沟壑之间又实在心有不甘。听说你急人之忧,又重同乡之情,忽然想到你或许可以眷顾我一下,和李将军美言几句,让我能在你的下面执鞭牵马,在李将军军中周旋。待大军大功告成,我也可以沾一些微末的功劳,能够忝居你的身侧。如果这样,那对我就是邱山一样重的恩德,我将永远铭记于心。当然,我知道这也是一种过分的愿望,可是还是想请你为我努力谋划。心中感慨,诚心希望你能宽宥我的造次,诚惶诚恐,希望你能不吝提携。”想起这封信,杨仲翔心中苦笑,大军惨败如此,哪有他说的大功告成,只在旦夕之间?当时,他也在心中一笑,不就是想在军中求个职吗,大军征战,职缺不少,何苦说得这么谦卑?得信之后,他很快和李宓将军说了。李宓将军首肯,说叫他来个管书记吧,县尉虽小,但缉盗捕贼,想必有些勇气谋略,军中正缺他这样的人。得命之后,杨仲翔立马回信,叫他速来军中。可是,还没等吴保安来到军中,大军便开拔了。可对吴保安来说,这却是幸事,否则,他也必将葬身此地,或者同他一样成为阶下之囚。
如今,他只能给吴保安写信,否则,他将连累其他俘虏不能吃饭。大家正在洱海边挖地垒墙,劈石运木,喂马劈柴,炼铁打刀,干的尽是苦事,别说三日不能吃饭,就是差了一餐之饭,都难支持。别的不说,为了自己和难友们的肚皮,他就得写这封信。但他并不指望素不相识的吴保安真能来救他,给他写信,只不过应付眼前之事罢了。再说,这封信能不能送达他手还很难说,或许,他已任职到期,调离其他地方或者回河北遂州老家去了呢。或许,这封信到了他的眼前,他虽不能援救,但请他回乡之后帮忙照顾双亲和家小,那也未尝不是好事。想定之后,杨仲翔展纸写道:“永固先生安好无恙。在成都时给你回过那封信,还没等到你的消息,大军已经开拔,深入苍山洱水,结果却败得惨不堪言。李将军阵亡,我成了囚虏。自念功名早已成为尘土烟云,在这里忍辱偷生,苟延残喘,无非是顾念双亲家小尚在,不敢先死,并怀想家国遥远,或许有朝一日能归故国乡里。我的才能比不上当年的楚国人钟仪,却还是和他一样兵败被俘;我的德行见识比不上殷商末代的大贤箕子,可还是和他一样做了奴仆之人。如今,我在洱海边放羊,有如当年在北海边牧羊的苏武;我宁可期待武帝在上林苑宫中射落大雁得到书信知晓苏武在北海的消息而帮助他得以回归大汉这类希望渺茫的事情,也不会做李陵那样在异国他乡出卖气节而得富贵的人。自从身陷蛮夷之地而成囚虏,备尝艰辛,供人役使,常常肌肤毁坏,血流满地。人生在世的艰辛,都已以身受之。想我以中原大地的世族之家,而沦亡为绝域蛮夷之地的囚徒,日月交替,暑退寒袭,日思夜想老父老母和亲朋好友身在故国而不得见,看见松柏之树便想起祖先的坟茔而不得洒扫祭奠,而今后自己殒命他乡也无法归葬祖墓之地。想到这些,常常心中发狂,胸中阻隔,痛不欲生,不知自己的泪水会在风中飘向何方。我在这里蓬首垢面,与乞丐无异,即使那些蛮夷之人,见到我的样子都会同情悲伤,叹息一番。我和永固先生,虽然未得谋面,互通款曲,而同为乡里贤达之人,风味相亲,志趣相投。如今,我常思及故人,也曾在梦里想象你的仪表。想到大军驻留剑南成都之日,意气风发,好像就在昨天。那时,承蒙你的问候,便乘间隙向李宓将军举荐于你。李公听说你的才名,心想你有勇气智谋,便礼请你为军中管书记。可大军启程去远,你还姗姗未到。如今想来,你这是门传余庆,祖上积善,老天照看,结果就因事耽误,不能入军,所以就能声名保全。如果当时你早早来到军中,就职李将军麾下,和我一起在幕府参军,那你也会和我一样身陷绝域,一同为囚。我如今力屈计穷,身在困厄,这蛮夷之地的风俗是战败被虏之人,可以让亲族前往赎买。寻常俘虏索绢二十匹,可他们认为我是杨相国的侄子,和众人不同,索绢一千匹。杨相国门第高不可攀,我这所谓的侄子是从远方攀附上的,遭逢这种苦难,很难告知他这个消息,只好写书告知你知晓。希望你得到这封书信的时候,再写一封信告诉我远在家乡遂州的伯父杨剑,请他召集亲友,凑集赎金,将我赎回,使我死后骸骨得以归葬故乡。远在蛮夷绝域之地,左思右想,能够指望的人只有你一人。我的伯父杨剑已经离开官职,书信难以寄达。今天的事情,还请你不辞劳苦,为我奔忙。希望你能像当年的齐国名相晏子一样,在出使晋国的时候遇到羁困的越石父,便解下座驾左边的一匹骏马,把他赎回;也希望你像当年宋国人不惜代价,前往楚国赎回因战被俘的华元。我知道类似的事情,即使古人高义,做起来也很困难。知道足下你名节特著,所以才有这个请求。如果你不哀怜我的处境,那我只有活着时候作为一个俘囚的奴仆之人,死了之后作为蛮夷之地的一个孤魂野鬼了,此生此世,再无指望!我知道这事让你为难,心中悲苦,我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想最后说一句:吴君,请你千万不要丢下我的事不管!”
写下这封信,杨仲翔在洱海周边四处辗转,继续为奴。那封信已经送出,但杨仲翔知道很难有什么结果,不过强人所难,给那位名叫吴保安的人徒增烦恼罢了。剑南偏僻之地的一个小小县尉,不过缉盗捕贼而已,能有多少积蓄?再说,自己的赎金可是一千匹绢,普通地方小官一辈子的俸禄也没这么多。至于自己的伯父杨剑,早已年迈,家里也不富有,即使吴保安得信之后给他写了信,他也不过只能召集族人,告知大家自己身陷南蛮绝域之地的消息而已。自己早已家道中落,为了在军中谋个职位,早已变卖家资,空无所有。族人得知消息,不过感叹唏嘘一番,对自己家里有点接济罢了,要凑足一千绢的赎金,那是万无可能的。但即使这样,也算不错,毕竟家人能因这封书信得到一些接济。而这,其实也是自己给吴保安写信的真实原因。他给吴保安写的第一封信,并没请他凑集赎金来赎他,不过请他给家里写信,让伯父凑集赎金送到蜀地之后,由他居中斡旋,前来赎买自己而已。他知道这不过是几句空话,若家里不能凑集赎金,吴保安自然不会勉强在意的。但主人请人看信之后,把那封信撕毁了,还将他打骂一番,让他重写,加上那些恳请吴保安一定要来赎他的话语。无奈,他只好写了上面那封信,寄出之后,想起来都有些害臊,怎么能用所谓的信义去要挟吴保安这么一个一素未谋面的陌生朋友呢?
书信被主人送出后,吴保安并不抱什么希望。但他也不甘终生为奴,一直在寻机逃跑。第一次逃跑,三天之后就被抓回,他被主人狠狠抽了一顿鞭子,饿了三天。半年后,他又逃跑第二次,数天之后被人抓获,主人把他毒打一顿,脚上戴了镣铐。从此以后,杨仲翔吃饭睡觉干活都戴着那副镣铐,慢慢断了逃亡的念头。转眼数年,赎买杨仲翔的消息和一千匹绢还杳无踪影,但大唐乱了的消息却传到了南诏和杨仲翔的主人耳里。从大唐传来的消息说,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和范阳节度使史思明叛唐作乱,率大军攻破潼关,进占长安,大唐天子李隆基逃亡蜀地。途中,禁军在马嵬坡发动兵变,杀死了宰相杨国忠和贵妃杨玉环。主人想,杨仲翔是杨国忠的侄子,杨国忠死了,就不会有人出那么多赎金来赎杨仲翔了。至于那个什么吴保安,一个小小的县尉,又是一个连杨仲翔一面都没见过的朋友,怎么会来赎他呢?如果要来赎,也早就来了。眼见获取赎绢无望,主人就把杨仲翔转卖给另外一个人。第二个主人把杨仲翔带都走的时候,第一个主人不忘嘱咐那人,看好这恶奴,他可是值一千匹绢的人啊,他想逃跑,千万别让他跑了。在第二个主人那里,杨仲翔呆了几年,度日如年,其间又逃跑了几次,都被抓回。没过几年,杨仲翔又被转卖给第三个主人,没过多久,又被转卖给第四个、第五个人……杨仲翔被不断转卖,除了那传说中的值一千匹绢的赎金,还因为他读书识文,能为主人记账作书,颇有价值,和一般的奴仆不同。但这个人不安分,老想着逃跑,也让主人不省心,所以他在每一个主人那里都呆不长。最后一次,杨仲翔被转卖给一个名叫南涧的地方。这个地方在苍山洱海之南上百里,离大唐的剑南之地更加遥远。没待多久,杨仲翔就再次逃亡。他清楚,要想回归故土,只有逃亡一条路,如果安分地待着,那他只有身死异乡,成为他乡之鬼。即使明知逃亡不成,会受到严厉惩罚他也在所不惜。大不了就是被主人杀了,如果注定身死异乡,早死一天,晚死一天又有什么分别。在南涧,他逃了三次,第三次逃亡被抓回,主人极其愤怒,把他捆绑在一根柱子上,让人用铁钉把他两只脚掌钉穿,在柱子上捆了三天。杨仲翔晕死过去,以为就此命丧他乡。但他还是活过来了,双脚上又和当年在第一个主人那里一样,多了一副镣铐,继续为奴。
原标题:《群山
雷杰龙短篇小说:记骨(一)》
转载请注明:http://www.tanglanga.com/mfsd/12057.html